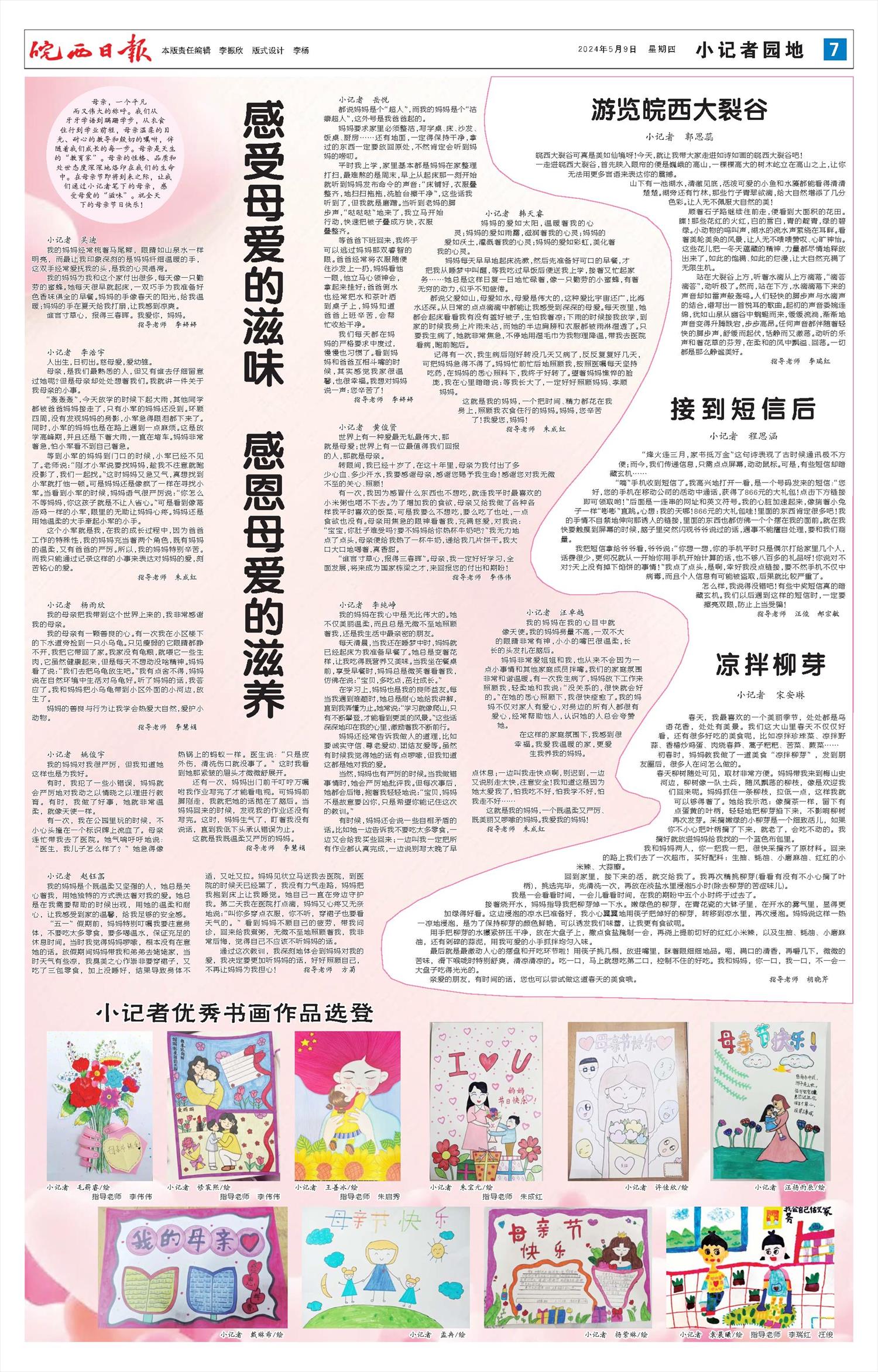05版:教体新闻
05版:教体新闻
- * 以剧为镜 逐梦绽放
- * 全市小语优质课教学比赛暨展示活动举行
- * 切实加强中小学美育工作
- * 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
- * 铝板琴奏响特色延时课
- * 爱心义卖欢乐多
- * 多彩科普活动 点燃科技梦想
- * 科学家讲堂开课
- * 送法进校园倾情护“未”来
- * 十八岁,梦想与你皆耀眼
- * 叶集区:积极推动教育质量再提升
 06版: 红土地
06版: 红土地
- * 回到金寨县果子园公社的十年
- * 麻埠寻古
- * 史河,从我身边静静流过
- * 符桥瓷歌
- * 酥饺铁锅状元鞋
 07版:小记者园地
07版:小记者园地
- * 感受母爱的滋味 感恩母爱的滋养
- * 游览皖西大裂谷
- * 接到短信后
- * 凉拌柳芽
- * 小记者优秀书画作品选登
转眼“小南岳文学社”已走过四十个年头,我很佩服那些记忆力好的人,四十年的往事都能浮现在眼前,而我作为“小南岳”的亲历者,却大多都忘却了,抑或是大脑内层太小的缘故。
我生在农村,祖辈农民,从未想过要玩文学,但有些事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上学那会儿,邻座同学包书纸是一张报纸,而那报纸上有个作者叫“金炳华”,写的什么我忘了。好奇心让我与邻座闹出了点动静,老师把报纸没收去了,数落了什么我忘了,但那句“金炳华,金从华,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戳到了我的心里,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想“玩玩”文学。
于是,我把天真的想法变成愚蠢的行动,其结果也是意料之中,文字没有变成铅字,却荒废了学业。但潜意识中那股倔劲还在:那就留着自己玩呗!
绝对是活猫碰到死耗子,1983年春《上海青年报》举办的一个征文活动,我的拙作居然获了个小奖,我不敢相信,很多人也不愿相信。
谢明信了,骑车跑到霍山二中要看报纸,拿着报纸,谢明脸上漾起两个酒窝,我要“玩玩”文学的信心就是从那一刻坚定的。
“小南岳”的成立也很偶然,九个懵懂的青年在文化馆西厢房,在书圣老馆长的提议下,连手都没有举,文学社就成立了,也许是天意,我记得那天是1984年“九九老人节”,预示着“小南岳”将天长地久。
“小南岳”为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两个专版”(刊发于《安徽日报》、《皖西报》)之后,引来省内外的一些知名作家、编辑。
许辉老师(后来的安徽省作协主席)也是那时在霍山与我不期而遇的,他在霍山采风时脚被磨破了,上客车时还是我帮他背上去的,他在散文《六安三日》(刊于《皖西报》)中特意说“感谢六安小伙子”背他上车。诗人刘祖慈也来霍山了,与诗人觥筹交错,不亦快哉,只是我那晚酒大了,酒话连篇,诗人当晚写下组诗《拔牙三章》,后来在省城见到诗人,诗人居然说他的《拔牙三章》是受了我的“酒话”启发。1988年盛夏散文家江流先生来了,他在一篇题为《盛夏赏小荷》中提到谢明、张宏雷和我,唉呀,能被大师提及,那是何等荣幸啊。
方雨瑞那时已是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但与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夏日的夜晚,他骑着摩托来到我宿舍(外面办公里面睡觉的那种),那晚九点多我正和谢明“侃”文学,见方兄深夜来访,甚是高兴。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房间正好有一瓶佛子岭大曲,可竟然找不出三个杯子,最后我只能用漱口杯子,一斤酒我和方兄一人一半,一包烟我和方兄一人十根,一袋铁瓜子,我和方兄一半,谢明一半(那时谢明还是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奶油小生),最后瓜子吃完酒也喝完了,方兄打趣道:瓜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多日,估计是方兄酒瘾又发了,他骑着电驴子又来了,那晚他是和谢明、达勇(文学社早期会员)一起来的,可我那晚酒已喝大了,房间的灯亮着,他们从窗户看到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担心会出事,便一边不停地呼叫,一边不停地拍打门窗,等到找来菜刀把门撬开,见我脸色红润,呼吸匀称才放下心。那夜酒自然是没有喝成。最后还是方兄调侃了一句:我们三个人可是见证了你的“生死”。
那时候我们之于文学,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在一篇小文写到,搞文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丑”。那时我们经常向大报大刊投稿,当然基本都石沉大海,不过也有欣慰的时候,谢明、宏雷和我三人的诗歌都多次在《诗歌报》上登过,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要知道那时候“盘”《诗歌报》比“盘”《安徽青年报》可难多了,就是北岛、舒婷、海子们也不是想上就上的。不怕丑的精神还表现在我们经常带着稿子去编辑部,有时让编辑老师讲得脊梁沟子冒冷汗,但细细一想又获益匪浅。我和谢明等也成了徐航(《皖西日报》编辑)、严成志(《诗歌报》编辑)、方雨瑞、罗会祥等老师家的常客,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几位老师的抬爱,以至于后来“玩”得很自信,“玩”到北京去了,文学社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中华读书自学成才”先进集体,吴南江被评为全国积极分子。
由于文学社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采风、讲座、改稿会等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1992年8月1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没有买到火车票,在合肥站候车厅溜达时,见谢明提个箱子过来了,巧了,他也去北京开会,他有张卧铺票,可能是“二不怕丑”的精神使然,我买了张站台票混上卧铺车厢,我只能隐匿在谢明铺位外的椅子上。
我和谢明说,这次我能见到大诗人叶文福,谢明先是羡慕,随即朗诵了诗人的名篇力作《将军,你不能这么做》,他那神情只有痴迷文学的人才能够流露出来。那次会议我还认识了《人民日报》社编辑徐怀谦,后来和他就有了书信来往,他出版的书,每次都给我寄,他的语言犀利、幽默、精妙、睿智,不愧北大的高材生,而他则说“没事,写着玩”。唉呀,不想大作家也把对文学的爱称为“玩”。2011年冬再次见到他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女儿准备出一本书,到时请我写个序,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又笑着说,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是写着玩的。我至今不明白他说的“玩”,是指我的还是指他女儿的。2012年8月22号,著名杂文家徐怀谦先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据朋友说他是前一天才拿到她女儿新书《花开的声音》,而他却永远地“悄无声息”了。我忽然想起他寄给我的一本书扉页上写着: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我不敢再想了。
徐怀谦的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也悲伤了很长时间,看来文学不是随便“玩”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玩”的,我以为应该像徐怀谦先生那样,要从“小我”走向“大我”,作家是有良知的,是有社会责任的。
四十不惑。“小南岳”诞生在沙漠地带,欣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绿洲,一群懵懂的青年开始崭露头角,一篇篇作品变成铅字;可喜的是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长满了灌木,吴南江、张宏雷等等一大批实力派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可贺的是近年来出现这样的现象:谢鑫著作不再等身,而是他无论如何也担不动了,且全是畅销书,已成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入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榜,两度获得“当当影响力作家”称号;沈俊峰已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数次获国家级大奖,单凭一部长篇小说《桂花王》就赢得大把的人气,目前《桂花王》正在搬上影视,不久的将来将会产生更大的共鸣;谢明从“小打小闹”到“获奖专业户”,作品青春、清新、亲民,又透着儒雅、深邃、哲思,凭借实力获得全国“散文十佳”,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三棵大树,迎风招展,引领风骚,引以为傲。
2022年9月,霍山县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给霍山的文学创作带来又一个春天,首任主席俞亮信心百倍,豪情满怀,硕果挂枝。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那人、那事、那文已是过眼云烟,但四十年的“小南岳”依然焕发着青春,她是一块里程碑,更是一块丰碑。
我生在农村,祖辈农民,从未想过要玩文学,但有些事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上学那会儿,邻座同学包书纸是一张报纸,而那报纸上有个作者叫“金炳华”,写的什么我忘了。好奇心让我与邻座闹出了点动静,老师把报纸没收去了,数落了什么我忘了,但那句“金炳华,金从华,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戳到了我的心里,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想“玩玩”文学。
于是,我把天真的想法变成愚蠢的行动,其结果也是意料之中,文字没有变成铅字,却荒废了学业。但潜意识中那股倔劲还在:那就留着自己玩呗!
绝对是活猫碰到死耗子,1983年春《上海青年报》举办的一个征文活动,我的拙作居然获了个小奖,我不敢相信,很多人也不愿相信。
谢明信了,骑车跑到霍山二中要看报纸,拿着报纸,谢明脸上漾起两个酒窝,我要“玩玩”文学的信心就是从那一刻坚定的。
“小南岳”的成立也很偶然,九个懵懂的青年在文化馆西厢房,在书圣老馆长的提议下,连手都没有举,文学社就成立了,也许是天意,我记得那天是1984年“九九老人节”,预示着“小南岳”将天长地久。
“小南岳”为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两个专版”(刊发于《安徽日报》、《皖西报》)之后,引来省内外的一些知名作家、编辑。
许辉老师(后来的安徽省作协主席)也是那时在霍山与我不期而遇的,他在霍山采风时脚被磨破了,上客车时还是我帮他背上去的,他在散文《六安三日》(刊于《皖西报》)中特意说“感谢六安小伙子”背他上车。诗人刘祖慈也来霍山了,与诗人觥筹交错,不亦快哉,只是我那晚酒大了,酒话连篇,诗人当晚写下组诗《拔牙三章》,后来在省城见到诗人,诗人居然说他的《拔牙三章》是受了我的“酒话”启发。1988年盛夏散文家江流先生来了,他在一篇题为《盛夏赏小荷》中提到谢明、张宏雷和我,唉呀,能被大师提及,那是何等荣幸啊。
方雨瑞那时已是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但与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夏日的夜晚,他骑着摩托来到我宿舍(外面办公里面睡觉的那种),那晚九点多我正和谢明“侃”文学,见方兄深夜来访,甚是高兴。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房间正好有一瓶佛子岭大曲,可竟然找不出三个杯子,最后我只能用漱口杯子,一斤酒我和方兄一人一半,一包烟我和方兄一人十根,一袋铁瓜子,我和方兄一半,谢明一半(那时谢明还是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奶油小生),最后瓜子吃完酒也喝完了,方兄打趣道:瓜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多日,估计是方兄酒瘾又发了,他骑着电驴子又来了,那晚他是和谢明、达勇(文学社早期会员)一起来的,可我那晚酒已喝大了,房间的灯亮着,他们从窗户看到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担心会出事,便一边不停地呼叫,一边不停地拍打门窗,等到找来菜刀把门撬开,见我脸色红润,呼吸匀称才放下心。那夜酒自然是没有喝成。最后还是方兄调侃了一句:我们三个人可是见证了你的“生死”。
那时候我们之于文学,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在一篇小文写到,搞文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丑”。那时我们经常向大报大刊投稿,当然基本都石沉大海,不过也有欣慰的时候,谢明、宏雷和我三人的诗歌都多次在《诗歌报》上登过,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要知道那时候“盘”《诗歌报》比“盘”《安徽青年报》可难多了,就是北岛、舒婷、海子们也不是想上就上的。不怕丑的精神还表现在我们经常带着稿子去编辑部,有时让编辑老师讲得脊梁沟子冒冷汗,但细细一想又获益匪浅。我和谢明等也成了徐航(《皖西日报》编辑)、严成志(《诗歌报》编辑)、方雨瑞、罗会祥等老师家的常客,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几位老师的抬爱,以至于后来“玩”得很自信,“玩”到北京去了,文学社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中华读书自学成才”先进集体,吴南江被评为全国积极分子。
由于文学社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采风、讲座、改稿会等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1992年8月1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没有买到火车票,在合肥站候车厅溜达时,见谢明提个箱子过来了,巧了,他也去北京开会,他有张卧铺票,可能是“二不怕丑”的精神使然,我买了张站台票混上卧铺车厢,我只能隐匿在谢明铺位外的椅子上。
我和谢明说,这次我能见到大诗人叶文福,谢明先是羡慕,随即朗诵了诗人的名篇力作《将军,你不能这么做》,他那神情只有痴迷文学的人才能够流露出来。那次会议我还认识了《人民日报》社编辑徐怀谦,后来和他就有了书信来往,他出版的书,每次都给我寄,他的语言犀利、幽默、精妙、睿智,不愧北大的高材生,而他则说“没事,写着玩”。唉呀,不想大作家也把对文学的爱称为“玩”。2011年冬再次见到他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女儿准备出一本书,到时请我写个序,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又笑着说,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是写着玩的。我至今不明白他说的“玩”,是指我的还是指他女儿的。2012年8月22号,著名杂文家徐怀谦先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据朋友说他是前一天才拿到她女儿新书《花开的声音》,而他却永远地“悄无声息”了。我忽然想起他寄给我的一本书扉页上写着: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我不敢再想了。
徐怀谦的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也悲伤了很长时间,看来文学不是随便“玩”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玩”的,我以为应该像徐怀谦先生那样,要从“小我”走向“大我”,作家是有良知的,是有社会责任的。
四十不惑。“小南岳”诞生在沙漠地带,欣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绿洲,一群懵懂的青年开始崭露头角,一篇篇作品变成铅字;可喜的是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长满了灌木,吴南江、张宏雷等等一大批实力派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可贺的是近年来出现这样的现象:谢鑫著作不再等身,而是他无论如何也担不动了,且全是畅销书,已成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入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榜,两度获得“当当影响力作家”称号;沈俊峰已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数次获国家级大奖,单凭一部长篇小说《桂花王》就赢得大把的人气,目前《桂花王》正在搬上影视,不久的将来将会产生更大的共鸣;谢明从“小打小闹”到“获奖专业户”,作品青春、清新、亲民,又透着儒雅、深邃、哲思,凭借实力获得全国“散文十佳”,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三棵大树,迎风招展,引领风骚,引以为傲。
2022年9月,霍山县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给霍山的文学创作带来又一个春天,首任主席俞亮信心百倍,豪情满怀,硕果挂枝。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那人、那事、那文已是过眼云烟,但四十年的“小南岳”依然焕发着青春,她是一块里程碑,更是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