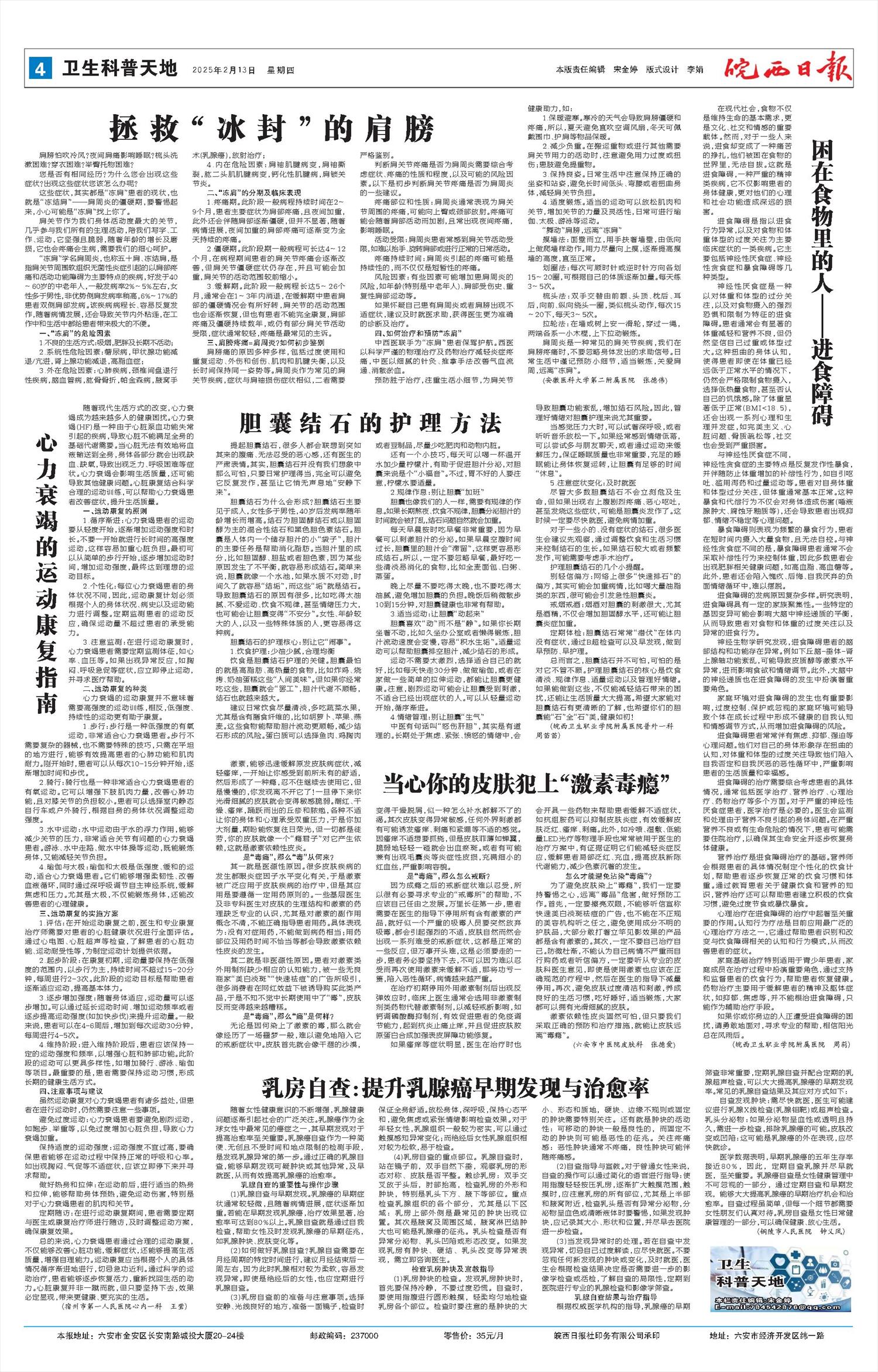05版:教育园地
05版:教育园地
- * 教育部修订《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 * 市教体局窗口多举措打造政务服务新标杆
- * 茶香润童心 剪纸显魅力
- * 全市首个乡村小学课题立项
- * 裕安区举办“中华魂”主题教育演讲赛
- * 爱的启航
- * 上学路上的遐想
- * 祖国在我身后
- * 走进束苑
- * “打”糍粑
- * 生日礼物
- * 教室里的生日会
- * 一堂有趣的课
 07版:茶文化专题
07版:茶文化专题
- * 茶之味·岁月沉淀的芬芳
- * 茗中上品六安茶
傅剑
塆楼组,是金寨县槐树湾乡长冲村一个高山地带的村民组,与南溪镇丁埠村的红畈组交界。我们来时的这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从塆楼经过,上葫芦岭,过红畈组,翻红旗山东寨门,上上下下,就可以出口直达立夏节起义红色遗址——丁埠大王庙。
塆楼,110户人家,散落在山顶、山腰、山脚下,420人。这里,山峰竞秀,绿荫覆盖,植被茂密,地僻人稀。一年四季,风景幽美,空气清新。拥有山场1000亩,野生茶园约400多亩,园地茶约50亩,并且繁植着大量野生的中药材,海拔均在300米上下,终年云雾缭绕,水气蒸腾,背靠的葫芦岭与红旗山,更在300至500米的海拔高度,三面环水,与南溪曹畈的九龙山,和槐树湾码头村的张公山,呈三角形隔湖相望,犄角呼应。
余述山,塆楼人,40多岁的茶老板,在古碑镇镇政府所在地二环路街道,开“皖西白茶”茶莊。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着近20年的“玩”茶经历,对茶的种类、习性、品味很有研究,从土壤环境、生长气候,到茶芽的采摘、制作、烘焙,到成品的存储销售,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好几次邀我去他的老家塆楼看看,因琐事缠身,屡屡失约。终于,在立冬过后一个气温回暖的大晴天,欣然邀伴前行。
汽车顺着山区水泥路慢行,左弯右拐,起起伏伏。时而村庄新居,时而荒岗坡地,时而陡峭悬崖,斗折蛇行。过了长冲村部,直下梅山水库叉河边,倏见一座白色护栏的新桥横跨河道之上,如长虹卧波。山色空澄,水天明净。两岸山影树色,倒映碧镜之中,如泼墨重彩的山水画。隐约可见九龙观上挺立的南天门,殿宇亭阁,红墙黛瓦;与隔河相望的绝壁千仞张公山,像一对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
过了这座桥,就踏进塆楼组地界。终于到达余述山家的村庄,建在山半腰,几户人家,楼房高耸,白墙红瓦,参差错落,房前屋后,干净清爽。塆前一口大大的池塘,水泛清光。配上四围护栏,赭石色仿古,相得益彰。站在门前晒场上,环顾四周,群山环抱,竹树稠密如锦缎,青苍中夹杂着块块翠绿和赭红,那红色,是枫叶燃烧似火的热烈,深浅变幻。放眼斜对面偏西的大山上,半腰深处,浮现两处白色楼房,是一上一下的两户人家。这使我想起“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想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想起“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中饭,在述山的大妈家,也是我邀约相伴而来的姨表弟本利的岳母家。今天是个好日子,恰逢老人家八十三岁寿诞,堂屋大圆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耳锅子,四围挤满了拼盘。佳肴夺目,香气盈屋。除了来客以外,全是留守的七十岁以上男女老人。也许是一辈子生活在塆楼这块幽静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饮着纯净的山泉水,喝着散发兰花香气的茶汁,吃着自己种植的蔬菜和大米饭,老人们个个精神抖擞,面目爽朗,畅谈不已。“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颇有山村乡野的古朴情趣。
屋外,山野空寂,层林尽染;屋内,举杯祝寿,笑语盈盈。边吃边聊中,述山的父亲,也算我的叔岳,告诉我,我们来时停车观景的新大桥边不远处,有一座老式吊桥,原先没修新大桥时,湾楼人到双石、码头、或响山寺、槐树湾乡政府,都要从吊桥往来经过,只能步行,不能通车,这头是塆楼,那头是看花楼;虽然现在都属于长冲村,听老辈人说,在闹革命时期,河这边湾楼归河南商城管辖,属于红区;河那边看花楼却归安徽六安县管辖,属于白区。那时,这河上连吊桥都没有,往来只有渡船工具。这吊桥,也是解放后,在大集体年代才建起来的。
“既然你这里红白区交界地带,肯定也有一些革命故事呀!”我惊奇地问道。“有呀!我们屋后葫芦岭上的三棺庙附近,还埋葬着一位红军赤卫队战士呢!”述山父亲答道。
我们小时候,总喜欢听大人们讲故事,听的最多的就是红军打毛排。有一次,述山的小爷(叔祖父)和四老太(叔曾祖)亲身经历看到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屋后葫芦岭二包子。原来,敌人用毛排运输食盐从金家寨至丁埠,经过塆楼地界的马包子,被红军赤卫队截获,然后集中在葫芦岭上的三官庙存放。敌人恼羞成怒,由国民党保安团头目黄英亲率一团人马,进攻三官庙,欲夺回食盐等物资。红军赤卫队12位战士,在葫芦岭二包子与敌激战。红军依托险隘关口的有利地形地势,居高临下,英勇抗击,激战至天黑。敌见久攻不下,天已渐黑,怕吃暗亏,随慌慌张张撤退而去。红军乘势追击,在树林里又俘虏几名掉队的敌兵。这一仗,敌人损兵折将,红军只牺牲了一名战士,被就地掩埋在三官庙后面,直至现在,都不知道姓啥名谁。
吃过午饭,正式开启塆楼美景的赏游。本利先带我参观这塆百年历史的老厅屋。至大门口,迎门一对石鼓,坐倚两侧门边,纹钉清晰可见。由于年长月久,略泛油亮光泽,用手摸摸,细腻滑溜。踏进门内,一张条状陈旧香案,横靠厅屋正面墙壁,正对大门。香案四脚,呈马蹄腿型状。环视根根圆柱,均有檩条榫卯相合,牵拉稳固,下托圆形石磴,上顶横梁。梁叠三层为架,层层两端雕龙刻花,与檩条榫卯契合,框架紧凑固实,架顶为脊檩,最为粗壮,檩两头雕刻向日葵花。其上屋平面,铺等距椽子,再覆满黑灰色小瓦。整间厅屋,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岁月气息,浸透着历经沧桑的感觉。
穿过老厅屋后墙侧门,便是宽敞院子,能看见正对厅屋的老堂屋,以及两边白墙瓷砖两层楼的人家。老堂屋,与两边楼房隔水沟独处,三级水泥台阶。跟前面厅屋对比,堂屋很像最近几年才翻盖的,墙壁内外白亮,但大门却是老式格扇式样,网格状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木质长匾,雕刻着“天赐鸿恩"四个大字,无题款和印章。屋内正墙上挂着“天地国親师位”的家神,是我们现在家家堂屋悬挂且流行的那种样式。家神之上,又叠挂一木质长匾,上刻“忠厚传家”,与门楣匾一样,俱呈古色古香之态。
游完老屋,我俩顺着窄窄的水泥路,朝屋后葫芦岭慢步而上。至岭脊一平坦路段停下,本利说,我们先下到沟底看“嫦娥奔月”瀑布,然后再上去望三官庙烈士坟。
站在葫芦岭上,俯视四周,岭之南为述山家敞亮的村庄、山地茶园等开阔地带;岭之北,背荫,树林茂密,灌木丛生。
我和本利翻过路边人设的木栅栏,顺着浓荫蔽日的羊肠小道,小心地往沟底下去。山道崎岖不平,时有声声悦耳鸟鸣,空山回荡。野生菖蒲、麦冬,像兰草一样郁郁青青,间或碰见野丁当柿子像小红灯笼,缀满枝丫,夺目诱人。低矮的灌木丛中,时时逢到或红、或紫的小果果,簇簇串串,挤满枝条,亮丽生动。突然,一阵阵牛铃响起,清脆悠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浓荫深处,不见牛影,只闻铃音。
终于下到沟底,一道壮观的瀑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呈现面前。高约数丈,飞珠贱玉,蓬松晶莹,奋不顾身,直扑深潭。潭不大,波纹层层,涟漪圈圈。水明石净,直视无碍。潭两壁绝崖,如刀砍斧劈,布满茵茵苔藓,有青藤翠蔓,网罩其上,蒙络摇缀。坐潭边石上,背靠飞瀑,耳听飞流击潭轰鸣,仰观两峰夹峙的一隙天光,不觉顺嘴而出:“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似觉洪荒万古,隐世千年。
本利告诉我,这次来得不巧又巧。因为每到春夏之季,雨量充沛之期,水势激荡,千军万马,争拥腾跃,似银弧,若匹练,直垂深涧,雷震山谷。雨霁云散,晴光朗朗,水势稍缓,瀑布若天女散花,又似嫦娥奔月,妙曼舞姿,意态丰韵。当其时,漫山兰草,花香扑鼻;樱花怒放,绮丽似霞。映山红,争艳斗奇,竞展妖娆。百鸟争歌,空山回荡,余音绕云。到这来玩的客人,赏着塆楼的美景,喝着刚采摘制作的散发着兰花香气的野生茶,那个美心美情,妙不可言。
说巧,是立冬之前几日阴雨绵绵,瀑布源头的红畈地界,四围四峦蓄储水量,万泉千溪,汇聚红畈,归拢龙井沟口,飞崖跌涧,使我有幸于涧底一睹龙井飞瀑的绝伦妙姿。
我们顺原路返回。行至岭脊快接近木栅栏时,突见一红衣女子,手拿柴刀,坐于石上,见我俩走近,先与本利打招呼,也是塆楼人,夫家姓张。因本利常走岳母家,自然早已熟悉。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本利问。
“放牛!”
“我们刚才下去时,听到阵阵铃铛响声,就是你家的牛铃啰!”
通过交谈得知,她家饲养12头黄牛,整天散放于山林里。岭脊路边的木栅栏,也是她家打桩捆扎的,以防牛群越岭乱跑或害人庄稼。
冬天天短,日渐西坠,倏忽傍晚。我与本利匆匆浏览了红畈境内几棵百年古树。偌大的山头上,碰见几户人家,还是老式石面墙基建瓦屋。在杨树湾一处向阳坡地上,遇见一位男性老人,躬腰蹲着,在蒜地除草。问答中,得知老人已78岁。孩子们都在省城买房定居。逢年过节,孩子把他接去省城。节期过后,他立刻赶回老家来,故土难离,乡愁牵心。他说,还是老家好哇,自在,清闲。守着三间老屋,种种菜,养养鸡,适量劳动劳动,舒坦筋骨,别提多自在、多爽心!这时,西下的夕阳,斜照在这片空寂的山地上,给老人、古树、老屋,以及门前菜园田地,都镀上一道金色光泽。时间,在这一刻,定格为一帧凝固沧桑记忆的画面!
夜晚,静静的灯光下,我回味着“皖西白茶”店老板述山弟对我说的话,也是代表了湾楼男女老少的心愿,就是希望上级政府或某位企业大老板,依托湾楼优质地理环境、红色故事、山水胜境等有利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出集茶叶培植与龙井飞瀑开发融为一体的观光旅游圣境;仿照“安吉白茶”的生产经营模式,房前屋后,广植白茶,层层梯地,间套果木,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档次。这样,塆楼人从此有事可做:栽植,护理,除草,施肥,修剪,采摘,制作,人人有事干,家家增收入,并带动其它农副产品流通畅销,为世人所知所喜。一旦开发成功,将与曹畈九龙山、码头张公山,形成环绕梅山湖上游自然生态旅游链,既各有特色风格,又锦上添花,异彩纷呈!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塆楼,愿你早成心愿!
塆楼组,是金寨县槐树湾乡长冲村一个高山地带的村民组,与南溪镇丁埠村的红畈组交界。我们来时的这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从塆楼经过,上葫芦岭,过红畈组,翻红旗山东寨门,上上下下,就可以出口直达立夏节起义红色遗址——丁埠大王庙。
塆楼,110户人家,散落在山顶、山腰、山脚下,420人。这里,山峰竞秀,绿荫覆盖,植被茂密,地僻人稀。一年四季,风景幽美,空气清新。拥有山场1000亩,野生茶园约400多亩,园地茶约50亩,并且繁植着大量野生的中药材,海拔均在300米上下,终年云雾缭绕,水气蒸腾,背靠的葫芦岭与红旗山,更在300至500米的海拔高度,三面环水,与南溪曹畈的九龙山,和槐树湾码头村的张公山,呈三角形隔湖相望,犄角呼应。
余述山,塆楼人,40多岁的茶老板,在古碑镇镇政府所在地二环路街道,开“皖西白茶”茶莊。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着近20年的“玩”茶经历,对茶的种类、习性、品味很有研究,从土壤环境、生长气候,到茶芽的采摘、制作、烘焙,到成品的存储销售,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好几次邀我去他的老家塆楼看看,因琐事缠身,屡屡失约。终于,在立冬过后一个气温回暖的大晴天,欣然邀伴前行。
汽车顺着山区水泥路慢行,左弯右拐,起起伏伏。时而村庄新居,时而荒岗坡地,时而陡峭悬崖,斗折蛇行。过了长冲村部,直下梅山水库叉河边,倏见一座白色护栏的新桥横跨河道之上,如长虹卧波。山色空澄,水天明净。两岸山影树色,倒映碧镜之中,如泼墨重彩的山水画。隐约可见九龙观上挺立的南天门,殿宇亭阁,红墙黛瓦;与隔河相望的绝壁千仞张公山,像一对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
过了这座桥,就踏进塆楼组地界。终于到达余述山家的村庄,建在山半腰,几户人家,楼房高耸,白墙红瓦,参差错落,房前屋后,干净清爽。塆前一口大大的池塘,水泛清光。配上四围护栏,赭石色仿古,相得益彰。站在门前晒场上,环顾四周,群山环抱,竹树稠密如锦缎,青苍中夹杂着块块翠绿和赭红,那红色,是枫叶燃烧似火的热烈,深浅变幻。放眼斜对面偏西的大山上,半腰深处,浮现两处白色楼房,是一上一下的两户人家。这使我想起“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想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想起“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中饭,在述山的大妈家,也是我邀约相伴而来的姨表弟本利的岳母家。今天是个好日子,恰逢老人家八十三岁寿诞,堂屋大圆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耳锅子,四围挤满了拼盘。佳肴夺目,香气盈屋。除了来客以外,全是留守的七十岁以上男女老人。也许是一辈子生活在塆楼这块幽静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饮着纯净的山泉水,喝着散发兰花香气的茶汁,吃着自己种植的蔬菜和大米饭,老人们个个精神抖擞,面目爽朗,畅谈不已。“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颇有山村乡野的古朴情趣。
屋外,山野空寂,层林尽染;屋内,举杯祝寿,笑语盈盈。边吃边聊中,述山的父亲,也算我的叔岳,告诉我,我们来时停车观景的新大桥边不远处,有一座老式吊桥,原先没修新大桥时,湾楼人到双石、码头、或响山寺、槐树湾乡政府,都要从吊桥往来经过,只能步行,不能通车,这头是塆楼,那头是看花楼;虽然现在都属于长冲村,听老辈人说,在闹革命时期,河这边湾楼归河南商城管辖,属于红区;河那边看花楼却归安徽六安县管辖,属于白区。那时,这河上连吊桥都没有,往来只有渡船工具。这吊桥,也是解放后,在大集体年代才建起来的。
“既然你这里红白区交界地带,肯定也有一些革命故事呀!”我惊奇地问道。“有呀!我们屋后葫芦岭上的三棺庙附近,还埋葬着一位红军赤卫队战士呢!”述山父亲答道。
我们小时候,总喜欢听大人们讲故事,听的最多的就是红军打毛排。有一次,述山的小爷(叔祖父)和四老太(叔曾祖)亲身经历看到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屋后葫芦岭二包子。原来,敌人用毛排运输食盐从金家寨至丁埠,经过塆楼地界的马包子,被红军赤卫队截获,然后集中在葫芦岭上的三官庙存放。敌人恼羞成怒,由国民党保安团头目黄英亲率一团人马,进攻三官庙,欲夺回食盐等物资。红军赤卫队12位战士,在葫芦岭二包子与敌激战。红军依托险隘关口的有利地形地势,居高临下,英勇抗击,激战至天黑。敌见久攻不下,天已渐黑,怕吃暗亏,随慌慌张张撤退而去。红军乘势追击,在树林里又俘虏几名掉队的敌兵。这一仗,敌人损兵折将,红军只牺牲了一名战士,被就地掩埋在三官庙后面,直至现在,都不知道姓啥名谁。
吃过午饭,正式开启塆楼美景的赏游。本利先带我参观这塆百年历史的老厅屋。至大门口,迎门一对石鼓,坐倚两侧门边,纹钉清晰可见。由于年长月久,略泛油亮光泽,用手摸摸,细腻滑溜。踏进门内,一张条状陈旧香案,横靠厅屋正面墙壁,正对大门。香案四脚,呈马蹄腿型状。环视根根圆柱,均有檩条榫卯相合,牵拉稳固,下托圆形石磴,上顶横梁。梁叠三层为架,层层两端雕龙刻花,与檩条榫卯契合,框架紧凑固实,架顶为脊檩,最为粗壮,檩两头雕刻向日葵花。其上屋平面,铺等距椽子,再覆满黑灰色小瓦。整间厅屋,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岁月气息,浸透着历经沧桑的感觉。
穿过老厅屋后墙侧门,便是宽敞院子,能看见正对厅屋的老堂屋,以及两边白墙瓷砖两层楼的人家。老堂屋,与两边楼房隔水沟独处,三级水泥台阶。跟前面厅屋对比,堂屋很像最近几年才翻盖的,墙壁内外白亮,但大门却是老式格扇式样,网格状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木质长匾,雕刻着“天赐鸿恩"四个大字,无题款和印章。屋内正墙上挂着“天地国親师位”的家神,是我们现在家家堂屋悬挂且流行的那种样式。家神之上,又叠挂一木质长匾,上刻“忠厚传家”,与门楣匾一样,俱呈古色古香之态。
游完老屋,我俩顺着窄窄的水泥路,朝屋后葫芦岭慢步而上。至岭脊一平坦路段停下,本利说,我们先下到沟底看“嫦娥奔月”瀑布,然后再上去望三官庙烈士坟。
站在葫芦岭上,俯视四周,岭之南为述山家敞亮的村庄、山地茶园等开阔地带;岭之北,背荫,树林茂密,灌木丛生。
我和本利翻过路边人设的木栅栏,顺着浓荫蔽日的羊肠小道,小心地往沟底下去。山道崎岖不平,时有声声悦耳鸟鸣,空山回荡。野生菖蒲、麦冬,像兰草一样郁郁青青,间或碰见野丁当柿子像小红灯笼,缀满枝丫,夺目诱人。低矮的灌木丛中,时时逢到或红、或紫的小果果,簇簇串串,挤满枝条,亮丽生动。突然,一阵阵牛铃响起,清脆悠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浓荫深处,不见牛影,只闻铃音。
终于下到沟底,一道壮观的瀑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呈现面前。高约数丈,飞珠贱玉,蓬松晶莹,奋不顾身,直扑深潭。潭不大,波纹层层,涟漪圈圈。水明石净,直视无碍。潭两壁绝崖,如刀砍斧劈,布满茵茵苔藓,有青藤翠蔓,网罩其上,蒙络摇缀。坐潭边石上,背靠飞瀑,耳听飞流击潭轰鸣,仰观两峰夹峙的一隙天光,不觉顺嘴而出:“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似觉洪荒万古,隐世千年。
本利告诉我,这次来得不巧又巧。因为每到春夏之季,雨量充沛之期,水势激荡,千军万马,争拥腾跃,似银弧,若匹练,直垂深涧,雷震山谷。雨霁云散,晴光朗朗,水势稍缓,瀑布若天女散花,又似嫦娥奔月,妙曼舞姿,意态丰韵。当其时,漫山兰草,花香扑鼻;樱花怒放,绮丽似霞。映山红,争艳斗奇,竞展妖娆。百鸟争歌,空山回荡,余音绕云。到这来玩的客人,赏着塆楼的美景,喝着刚采摘制作的散发着兰花香气的野生茶,那个美心美情,妙不可言。
说巧,是立冬之前几日阴雨绵绵,瀑布源头的红畈地界,四围四峦蓄储水量,万泉千溪,汇聚红畈,归拢龙井沟口,飞崖跌涧,使我有幸于涧底一睹龙井飞瀑的绝伦妙姿。
我们顺原路返回。行至岭脊快接近木栅栏时,突见一红衣女子,手拿柴刀,坐于石上,见我俩走近,先与本利打招呼,也是塆楼人,夫家姓张。因本利常走岳母家,自然早已熟悉。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本利问。
“放牛!”
“我们刚才下去时,听到阵阵铃铛响声,就是你家的牛铃啰!”
通过交谈得知,她家饲养12头黄牛,整天散放于山林里。岭脊路边的木栅栏,也是她家打桩捆扎的,以防牛群越岭乱跑或害人庄稼。
冬天天短,日渐西坠,倏忽傍晚。我与本利匆匆浏览了红畈境内几棵百年古树。偌大的山头上,碰见几户人家,还是老式石面墙基建瓦屋。在杨树湾一处向阳坡地上,遇见一位男性老人,躬腰蹲着,在蒜地除草。问答中,得知老人已78岁。孩子们都在省城买房定居。逢年过节,孩子把他接去省城。节期过后,他立刻赶回老家来,故土难离,乡愁牵心。他说,还是老家好哇,自在,清闲。守着三间老屋,种种菜,养养鸡,适量劳动劳动,舒坦筋骨,别提多自在、多爽心!这时,西下的夕阳,斜照在这片空寂的山地上,给老人、古树、老屋,以及门前菜园田地,都镀上一道金色光泽。时间,在这一刻,定格为一帧凝固沧桑记忆的画面!
夜晚,静静的灯光下,我回味着“皖西白茶”店老板述山弟对我说的话,也是代表了湾楼男女老少的心愿,就是希望上级政府或某位企业大老板,依托湾楼优质地理环境、红色故事、山水胜境等有利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出集茶叶培植与龙井飞瀑开发融为一体的观光旅游圣境;仿照“安吉白茶”的生产经营模式,房前屋后,广植白茶,层层梯地,间套果木,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档次。这样,塆楼人从此有事可做:栽植,护理,除草,施肥,修剪,采摘,制作,人人有事干,家家增收入,并带动其它农副产品流通畅销,为世人所知所喜。一旦开发成功,将与曹畈九龙山、码头张公山,形成环绕梅山湖上游自然生态旅游链,既各有特色风格,又锦上添花,异彩纷呈!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塆楼,愿你早成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