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针密线 练达圆转
——读黄丹丹小说《雨水》
皖西日报
作者:杨华成
新闻 时间:2022年05月10日 来源:皖西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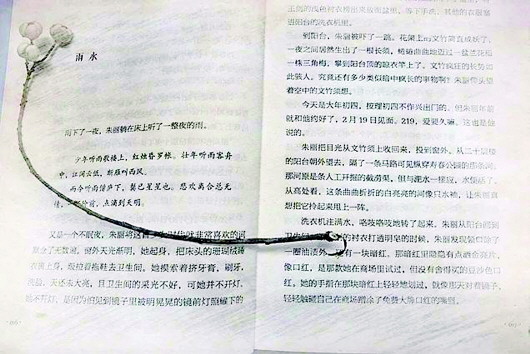
黄丹丹很是注重小说的构架与布局。《雨水》的情节,是随着女主朱丽的意识流动展开叙事的,线索交错,场景变换,初读如入迷宫,仿佛一次“陷入”,不能自主辨别方向,只好乖乖跟着作者这位“向导”的脚步走。但走出来回头一望,在朱丽与微信中的“他”约而未会的时间线上,穿插植入了她与王剑相爱、结婚、生活变故与“闹掰”的完整过程,小说情节又觉不难把握。当双线交叠时,小说卒章显志,作者要表达的意旨就明了了。情节的开合收放见出作者文笔的老练与轻灵,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自信。
黄丹丹也是心理描写的能手。朱丽夭折了儿子大山:“她就像被绑在一块大石上给沉了潭,就感觉身体不停地往下坠,往下坠,无法呼吸,无法呼救,既踏不到底,也见不到光。”痛苦到麻木与绝望时,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感受,写得到位,让读者也似乎沉溺其中了。作为女性人物,“沉潭”的比喻还有另一种因由的恰当,仿佛自叹这是命运的“刑罚”。
朱丽痛失儿子那段日子,开明的婆婆有意拉她去学唱戏,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减轻她的痛苦。朱丽的心理面貌是:“唱戏真好,上了妆,换了行头,水袖一摆,就成了杨贵妃:‘人生在世如春梦……’成了杨贵妃,就能忘了自己的疼了。”这种根据小说情节就近取譬的写法,读来类似散文写作中的移步换景,使情节推动流转自如,妥帖自然。
朱丽和王剑由“闹掰”到复合,作者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微妙的心理逻辑。“‘这下你解放了,可高兴?’王剑似乎并不觉得他们这对离婚不离家的夫妻就不能拌嘴,就像朱丽也不觉得把他伺候得跟个爷似的有什么不对。”如果说,他俩微信上的“重逢”巧合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貌离神合,或者说,他们在相处中早已冰释前嫌,那么约而不见的情节安排就补全了这一逻辑的合理性。
黄丹丹在小说构思中注重细节上的伏笔与照应。开篇不久她写:“花架上的文竹简直成妖了,一夜之间居然发出了一根长须,蜷蜷曲曲地迈过一盆兰花和一株三角梅,攀到阳台顶的晾衣竿上了。文竹疯狂的长势如此骇人。究竟还有多少类似暗中疯长的事物啊?”这段描写不是信手涂抹的闲笔,读者不难明白,这与文中朱丽发现王剑衣领上的口红印有关。小说结尾,作者也不忘带上一笔:“文竹的新芽似乎长得更长了,在晾衣架上颤巍巍地往上伸展着。”留心还会注意到另一处描写:“从高处看,这条曲曲折折的白亮亮的河像只水袖,让朱丽真想把它拎起来甩上一阵。”后文跟着婆婆学唱戏的情节呼应这一细节,并且也写到她“水袖一摆”的想法。“浑然”与“纤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取向,“浑然”强调贴近真实,拒绝刻意雕饰。但在深厚妥帖的生活表现同时,匠心的体现使作品更为鲜明集中,更有艺术风采。
黄丹丹的小说读着有宁静感。她没有沿着“开端——发展——高潮”这条线走,不着意在事件的激烈冲突中表现主题。她似乎很迷恋表现一种错综纠葛的情节样貌,在峰回路转中引领读者探寻到结局,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她的小说语言也不失“静”的气质,不矫饰,不夸张,细腻温婉,轻灵宛转,摇曳生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