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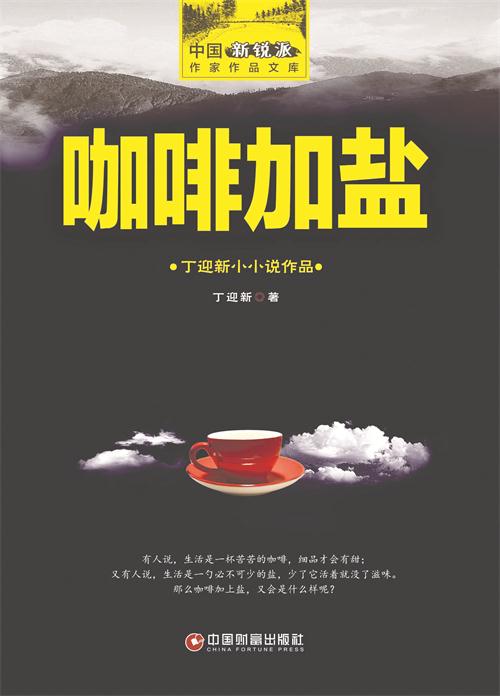
我曾在小说集《杠打老虎鸡吃虫》的后记中坦诚写到自己对当下文艺圈的看法,引起一些人的猜测和误解,但也有人表示赞同,这其中就包括晓晓。
记得在作协组织的一次笔会活动中,我和晓晓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周围香火袅绕,一片纷扰,与会者的脸上都写满了对文学的虔诚。晓晓说:文学创作,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种对文学由衷的敬畏之心反而显得有容乃大。
在众多的文友中,晓晓似乎是个“异类”,很少参与本地圈子活动,也很少与大家交流沟通,不知是刻意回避,还是因为生活所迫?
算起来,最早与晓晓“打交道”,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常常在报端上拜读他的作品,开始只知道他是舒城作家,名字很精巧,像两个跃动的音符,富有乐感,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后来逐渐获悉他的一些情况:晓晓的原名叫丁迎新,晓天人,当兵退伍后,分在舒城县酒厂工作,当过化验员、销售员和门卫,甚至烧过锅炉,后来连锅炉也没得烧的了。下岗后,一纸“高中文凭”让他四处碰壁,只能在家带孩子写写稿子赚取微薄的稿费,早上和晚上还得从城西兑大馍到城东卖,自行车上绑个大筐,他不敢大声叫卖,只是到处瞎转悠……
知道了这些,我对晓晓就不觉得奇怪了。
汉字写作一直有含蓄、节制的优秀传统,只是到了当代被打破,当下愈演愈烈到滥情书写,各种张扬的文字充斥眼球。晓晓的文字对于这种一路狂欢式的写作,是一种反叛。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韩进评价说,读晓晓的散文,完全颠覆了他憨厚质朴的农民形象,笔下流着炽热的血,有一种久违了的金刚怒目的文人反叛。晓晓写社会现象,写家庭教育,写爱人情感,写所见所闻,都习惯逆向思维,用反讽的手法,描写社会底层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最质朴的情怀理想,揭露现实的混乱和人性的异化。
《小说月刊》首席编辑何光占说,晓晓是安徽小小说界的中坚力量,他长于发现生活里耐人寻味的细节,甚至是悖论的现象,那些细节和现象连接起来,总能延伸到生活的地平线之外,醒目的陌生中有熟悉,看似熟悉,其中又有惊心的陌生,熟悉与陌生的交织开拓了许多生存的可能,进而为人们提供和记录了鲜有的经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疏利民说,晓晓作品如山野之风,清新自然。慢慢咀嚼,就像吃农家菜园里的自家菜,原生态,无污染,吃起来,有滋有味,不失大自然的原味,唇齿留香。这种原生态的创作是生活在大都市里人很难读到的自然味道。写真人、真事、真情,没有半点虚假和做作,在现代浮躁的社会实属难能可贵。从舒城大山里走出来的晓晓像小草一般的坚韧,如小草一般通透,像小草一般的豁达,凡事力求完美。看得开放得下,自信豁达,坦荡真诚,心存感恩,抛却纷纷扰扰,恩恩怨怨,也活得自在潇洒。
晓晓在创作上获取了很多的成绩,这些成绩大多不为人知,如果换个主人,也许会被炒得热火朝天。对于他来说,一个人的舞台恰恰更能让他投入。一个作家,写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对生活永不止步的勘探,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注。
做到此,文字就会活在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