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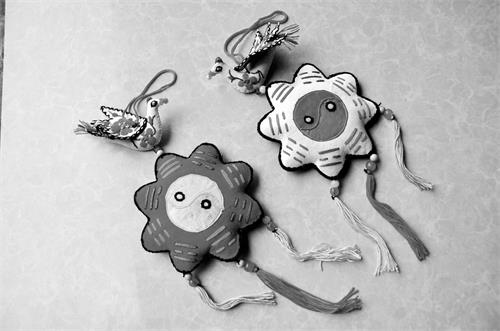



时光流逝,不觉间,外婆离开我们近四十个年头了。每每想起外婆,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温暖划过,外婆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这记忆的底片,使我难以忘怀,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清晰。
我的思绪,随着外婆人生的河流溯源而上。外婆祖籍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姓周,名琪珍。外婆属鼠,生于1900年,卒于1980年。
儿时的记忆,大多是和外婆牵连在一起的,故对外婆小脚的印象尤为深刻,用“三寸金莲”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记忆中的外婆从来不穿袜子,用的都是裹脚布,每晚必要泡脚。我常在庭院的晾衣绳中,看到两条长长的白色裹脚布,随风飘荡。
“三寸金莲”最早出现于唐末宋初时期,是古代妇女传统习俗的极端发展,人们把裹过的脚称为”莲”。有学者认为,小脚之所以称之为金莲,应该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方面加以考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至于在“莲”前加一个“金”字,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金莲”当也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吧。
据母亲说,外婆祖上原是舒城县大户人家。清朝末年,受战乱影响,家道日渐中落,外婆出生时,更是举家为艰。外婆很小便缠了足,只为将来嫁个好人家。虽如此,外婆母家也是多方打听,才忍痛把外婆许给了毛坦厂镇开蚕丝颜料店的后姓少东家一一后先宇(我外公)做童养媳。
外婆三四岁时就到外公家,当时还是封建的旧社会,故而外婆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外婆洗碗,因为岁数小,站在小板凳上,不小心摔倒了,额头磕破流了好多血。老太(外婆的婆婆)从锅洞里抓了一把柴灰,摁在外婆的伤口上,不许外婆哭出声。这件事给外婆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多年后,外婆每次和母亲提及此事,都有泪水从眼中沁出。
成年后的外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温和,是位贤良淑德、极有主见的人。十八岁和外公圆房后,不知是何原因,婚后十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外公虽是后家独子,却没为此而嫌弃外婆,可能与外婆从小青梅竹马的感情有关罢。直至28岁时,外婆才有了大姨,两年后,母亲又相继出世,外公心里很是欢喜。此后,外婆一生便没生养了。
外婆虽不识字,但心里世事洞明。接人待物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这许是跟外婆从小生活在外公家,耳濡目染有很大的关系。外公祖上是经商世家,为了躲避战乱,从皖南搬迁到毛坦厂镇落户。外公的母亲是毛坦厂镇“方、黄、刘、蔡”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姑娘(老太,38岁就去世了)。所以,外婆虽是童养媳,但外公家优渥的家境及良好的成长环境,也成就了外婆是位不凡的人。
外婆年轻时就信佛,有了母亲不久,开始吃长素,烧香拜佛,菩萨心肠,乐善好施,是毛坦厂镇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在母亲八岁那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妇人(丈夫去世了),带着几个孩童,从外地跑反逃难到毛坦厂,寻到了外婆家。外婆看到其中一个约摸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怯怯地躲在妇人身后,虽然饿极了,也不好意思伸手接外婆递来的东西吃。外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收留了他们一家。也许是缘分吧,后来,外婆正式认领了这位小男孩为养子,还请了几桌客。他就是我的大舅,今年93岁,现居淮南田家庵。
外公过世后,外婆更是虔心向佛。因为信佛,外婆一生中朝过两次名山,一是安徽九华山,二是西岳华山。信念与坚韧,是小脚外婆登临绝顶的因素,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因子。
在我的成长中,外婆对我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小时候外婆总是告诫我: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让别人看到口中的食物;要笑不露齿,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写字时一定要坐正身子,头不能歪等等。
在外婆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或许有“三寸金莲”小脚的女人不足为奇,但从小生活在皖西大别山里的外婆,因解放后儿女工作生活在外地,因此,外婆靠着一双小脚常年独自(或带着年幼的我)坐火车从北到南,转经北京、蚌埠、再到水家湖(淮南),每次至少两三天的行程,就这样,外婆始终奔波在儿女之间。
母亲每次和我谈及外婆的这些往事,都感慨万千。外婆的慈悲善良,既是她身上最好的风水,也是她人性渡口永远温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