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培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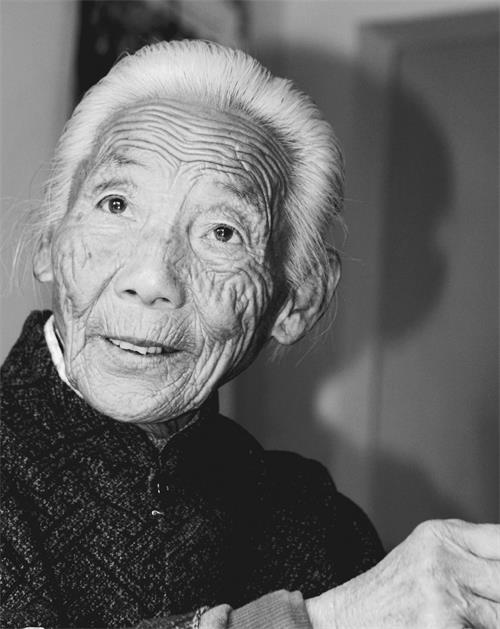
从和畅园出来,有人提议走一走散散酒气,走走就走走,我们仨歪歪扭扭地沿着佛子岭路一路向西晃悠。
边走边聊,兴致高起来,嗓门也大起来,吐纳之间皆有酒气肆意流窜。好在这一片并非闹市区,又加之乍暖还寒时节,路上行人少之又少,倒也正适合我们这类平时扯闲篇酒后净胡扯的主放浪形骸。过了博物馆,灯火更加暗淡。有人站在路边愣怔了一小会,突然冒出一句:“这到哪儿了?”
“前面不远,梅山路…”呦嗬!义森头脑蛮清醒的,晚间席上没少见他端杯子,而且是频频举杯,人家几句“北方人豪爽”,其更加得意忘形,几欲先醉。
记得去年冬一次临时小聚,义森说:人言在先,不好爽约,不能来了。酒过三巡,“吱呀”一声门开了,来的正是义森。但见其红着脸蛋,敞着羽绒服,平日斜挎的皮包吊在胸前,跌跌撞撞来到近前。说也神了,义森一眼就认上了一直以茶代酒的蓝总,拽着他要干一大白。蓝总接了个电话,匆匆逃也似的夺门而去。甩了一句“我徒弟全权代表我……”好么,就这一句又让义森逮着了把柄,死活跟“徒弟”喝一杯方了局。
喝了两场,本以为那晚他喝醉了,下了楼,我陪着他走了一段,他居然拦了一辆出租车,恁是帮我付了车钱。
不得了,义森这酒量不得了!可是义森爱喝酒好热闹,但不嗜酒。
义森喝酒,义森打牌,义森时不时飙歌,义森痛痛快快活在人间。一次有位文友实在忍无可忍了,问:“张老师,我一直好奇你应酬这么多又爱玩,文章是啥时候写的?”义森被人家美女这么零距离逼问,羞赧着回了一句,“抽空写……抽空写……”
其实,哪里是“抽空”,分明是“每晚写”,兀兀穷年,夜色暗淡了星光,灯光漂白了夜色,水上公园的岸柳和疏梅都记得义森为小说中某一个情节而慢踱的步子。
他有一个练习本子,上面密密麻麻排着行草,不是文稿,而是拟定的提纲,他按照此计划,一天几千字,一月几万字,一年几十万字。别人的梦想始终在远方遥不可及,义森这样一天一点迈进,终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