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圣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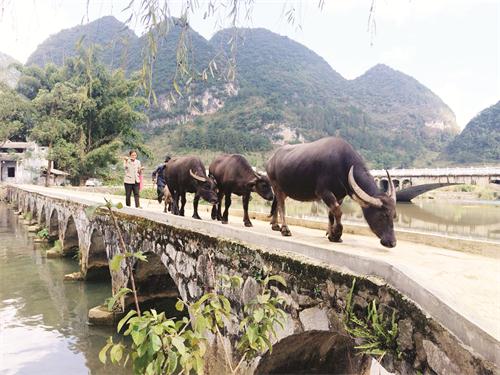
我出生在叶集,那时还是一个小镇。我的童年是在叶集五里长街南头一个土墙草顶的篱笆院里长大的,那时候父亲在遥远的河南某矿上工作,很少回家,母亲一个人带着儿女度日。
我的母亲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说不好花言巧语,却总能够怀着善心去帮助别人。街坊邻居,亲朋好友,谁有了困难,母亲自己再难,也会想方设法去帮人家一点什么。母亲说不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样文绉绉的话,但她知道帮助人是一件积德的事情。她教育孩子们说,过日子别光顾着自己,一定要善待他人、帮助他人。
一次,一个过路的老太太走进我家院子。母亲说,您找谁呀?老太太说,大妹子,我不找谁,我口渴的厉害,想找口水喝。母亲倒了一搪瓷缸子热水,招呼老人家坐下慢慢喝。那位老太太看起来非常疲惫,准备离开的时候,母亲看出她腿部的软弱、身体的摇晃、心跳的慌张。善良的母亲拉住她,说您等一下。她从藏在卧房中的糖罐子中挖出仅有的一勺儿红糖,倒上开水,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水,双手递给那个老人。那老太太受宠若惊,感动得几乎流泪,她说,我坐月子都没有喝过几碗糖水,今天遇到不认识的你,你真是个好心人呐。
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对母亲的糖罐子经常虎视眈眈,却总是可望不可即。糖太金贵了,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才舍得给我们嘴里塞一块糖疙瘩,或者在稀饭碗里放两勺。现代的娃娃,永远不会理解那个年月糖对一个孩子的诱惑。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于是,母亲给我讲了赵大妈的故事。
母亲说,那时候家里穷的啊,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经常到了饥肠辘辘的时候,摸摸米桶,空空的;揭开锅盖,空空的!经常在别人家吃饭的钟点,自己像个无头的苍蝇,这撞一头那撞一头。大人吧,还能忍忍,可几个孩子呢,眼巴巴望着母亲。有时母亲跑到人家薅尽的蔬菜地里翻翻土,看看能不能找几块遗漏的菜根,有时母亲跑到野地里看看能否找到能充饥的野菜,或者捋几把无毒的树叶子,几个孩子就一直围在锅台边,等着母亲回来,等着一点什么下锅,好填填肚子。
实在难了,什么吃的也找不到,母亲只得去跟邻居借一点。但是,家里长期那个样子,邻居家也不好过,有人就不愿借怕你还不上,母亲最怕看脸色,她宁愿钻到地缝里,也不想看到别人为难的脸。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出门借粮的。而邻居赵大妈,只要见母亲端个小盆过去,就知道家里实在过不掉了,总会在浅浅的米坛子里,舀那么一点给母亲。母亲的感动在骨子里,她最清楚人在难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点滴之恩对需要的人是多么重要。母亲说,谁能没有个难处,在别人难的时候帮助一下,老天都看着呢,老天不是睁眼瞎。
母亲一生贫困,但她的善良和爱从不贫困,母亲一直叮嘱我们,不管谁家遇到沟沟坎坎,能帮就帮一把,她的古道热肠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她用言行给了儿女最好的示范,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爱和尊重,并且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践行。
母亲儿时读过私塾,有些文化,对孩子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她支持每一个孩子读书学习,家庭经济无论怎么紧张,她没有让一个孩子辍学。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七十年代高中毕业生,老四、老五是八十年代读完高中。我在校那会儿,招生比例很低,大学十分难考,我所在的学校“黑窝”是一年一年常有的。我母亲说,你只管上,一年不行复习两年,两年不行复习三年,上到什么时候我供到什么时候。我当年还算争气,没有复习过,第一年应届就考上了大学。母亲心中丝毫没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概念,她支持孩子读书,只有一个朴素的概念,肚子有知识的人做人做事不一样。“读书明理”她说不好,但她知道粗鲁的人、扎扎拉拉的人往往没文化,母亲希望孩子都能成为通情达理的人。
等到孩子们参加工作了,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能贪心。在母亲心中,有吃的有喝的就是幸福。“幸福”一词的概念在母亲心里头实在简单,人生在世就是吃饭穿衣,能自食其力了,不用为衣食担忧了,就桃花开了,春天来了。母亲心中最美的春天就是米缸里有存粮,菜园里有好菜,箱子里有新衣服。
我们兄妹五个,在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勤俭节约,各自在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够踏实工作勤奋敬业,平淡而幸福地生活。
母亲,平凡而伟大,她用最质朴的生活之道,给了我们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母亲的教诲是最有价值的生命礼物,我们要把这份厚重的礼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引导子女把良好的家风和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以优美的风姿行走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