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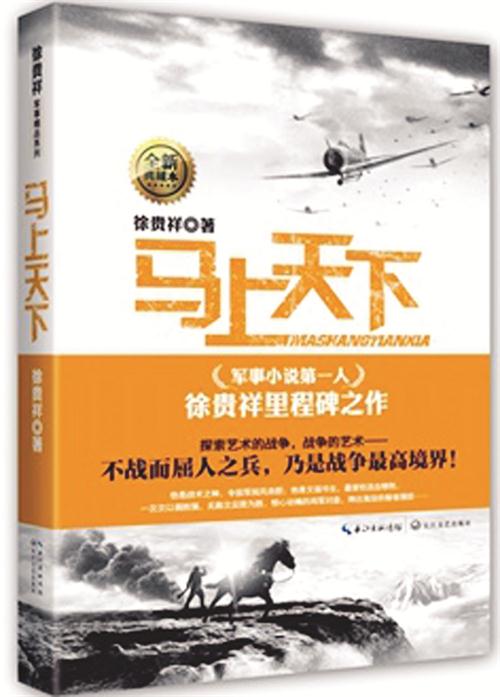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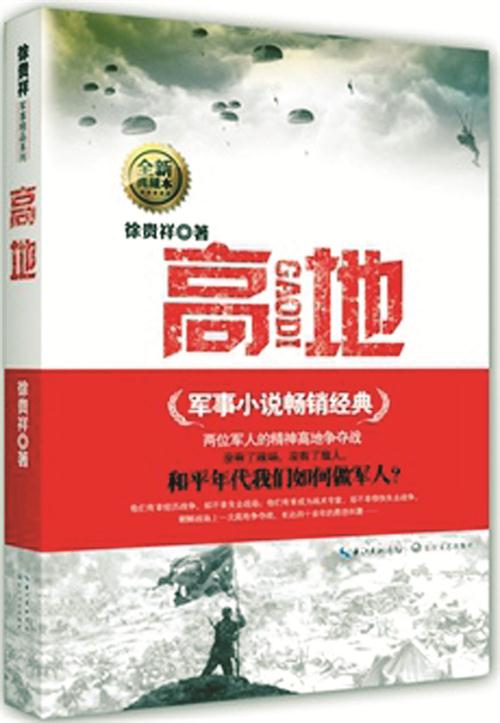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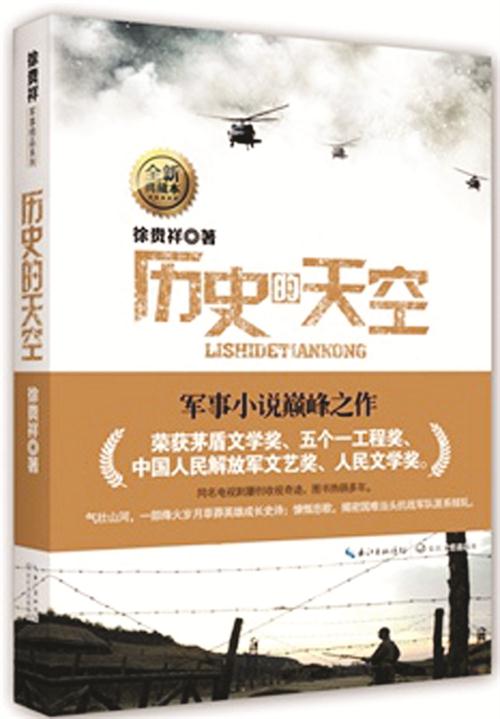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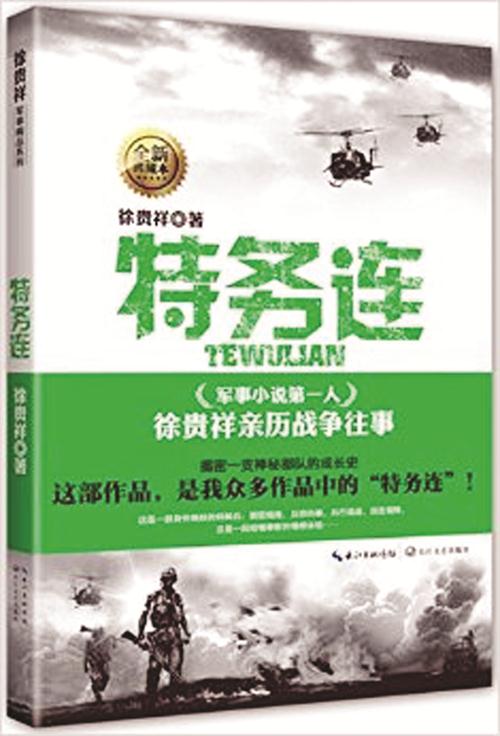
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临时驻扎在广西扶绥县,我们九连住在山圩农场。有一天,通信员通知我开会,到了连部才知道,原来是接受作家采访。采访我的作家戴着眼镜,军装上绿下蓝,空军的。我以为他要了解我在“长形高地进攻战斗”荣立三等功的事迹,于是兴致勃勃娓娓道来,哪知道每当我提起“长形高地进攻战斗”就会被他打断,他反反复复只问我在G城战斗中送饭的事情,这让我有点失落,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那次送饭的情况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没过多长时间,记得还是在山圩农场期间,有一天指导员赵蜀川把我叫了过去,乐呵呵地递给我一本名叫《解放军文艺》的书(那时候我们把装订成册的纸张都称为“书”),我惊疑地打开,指导员指点说,这里。我找到“这里”——《铁鞋踏破千重山》,特写,作者刘田增。刘作家的文章详细地记叙了龙怀富、汪柏昆和我火线送饭的事迹,最后几句话我终身难忘——火炮怒吼,映红了夜幕,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我们亲爱的新战士,来自淮北的小徐兄弟,进入香甜的梦乡,脸上洋溢着稚气的笑容。《列宁在1918》里的那个英勇的瓦西里,在押送粮食回到苏维埃之后,睡梦不也是这么香甜吗?
尽管我不是来自淮北,而是来自皖西,但是这篇作品还是令我感到荣耀。并且,就是这篇作品,激活了我的文学梦。要知道,在参军之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还模仿《伤痕》写过一篇小说,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
进入休整状态,我成了连队的一名业余报道员——因为我们炮团九连被广州军区授予“炮兵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我们的二班副王聚华是二级战斗英雄,所以指导员要求我们,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都拿起笔来写报道,写回忆文章。那一阵子,我热血沸腾,主要是以我们连队、特别是以王聚华的事迹为书写对象,马不停蹄地写呀写,先后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和《广西日报》发表《山岳丛林炮兵游击战》、《难忘的夜间战斗》等文章,写着写着就小有名气了,先后抽调到团里、师里、军里创作组,参加各类写作学习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扶绥东门师部,还见到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的编辑雷抒雁,印象中他戴着很厚的眼镜,手里夹着烟,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怎样写诗。具体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小黑板下面的红土地上扔了很多烟头,雷抒雁削瘦的脸庞在诗情中和夕阳下,闪闪发光。部队从广西回到中原之后,我就从《解放军文艺》上读到了他的诗作《甘蔗和孩子》,以后就特别关注他,又读过他的著名诗篇《小草在歌唱》。
幸好有了第二次参战经历。1984年夏天,我作为一名政工干部,随本部侦察大队赴云南边境轮战,在另外一片丛林里摸爬滚打一年多,深入地体验了战争,也深入地体会了文学。那个期间我写了很多小说,当时投稿,基本上泥牛入海,意外的惊喜是在战后,从前线回来后,这些作品陆续发表。
1987年夏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凌行正率领该社部分编辑到我所在的集团军召开“中原笔会”,带去很多编辑和作家。我那时候在军政治部组织处当干事,负责勤务保障。集团军首长非常重视那次活动,机关和部队夹道欢迎,又在大礼堂搞了一个隆重的见面会,作家和编辑登台亮相,凌行正、金敬迈、袁厚春、佘开国、刘立云、王瑛……我站在礼堂后门口,一方面观察着四周的警戒情况,同时远远地注视着那些亲切的身影,我真想跑到后台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文学骨干,我写过小说,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但是,我不能,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一度是我崇高的理想。后来我作为基层业余作者,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对《解放军文艺》处理稿件不及时、答复作者缺乏耐心提了意见,当时在场的有王瑛和刘立云,两个人都很重视,追问我具体是哪一部作品。中原笔会结束后,不到半个月,我就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来信,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稿子被耽误的原因,同时还有退稿,稿子上密密麻麻都是批注,原来,这篇稿子因为层层送审,一直处在用和不用的权衡之中,所以被耽搁了。
1991年秋天,我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之后,在解放军出版社帮助工作,业余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写好后一直拿不定主意往哪里投稿。济南军区有个作者叫梁丰,当时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帮助工作,我们几个外地来的“老帮”经常聚到一起玩,梁丰听我说了《弹道无痕》的构思,觉得挺好,看了稿子更觉得好,就拿回去给陶泰忠,陶主编当天看完,非常高兴,说意外地发现一个作家,潜力很大。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几个需要修改的地方,又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我就把几个稿子送给他,陶主编选了一个短篇《一段名言》,做了当期的头条,接下来的一期,又是《弹道无痕》做了头条,就这样,我和《解放军文艺》正式接上头了。
1997年夏天,《解放军文艺》编辑王瑛约我写一个古战争题材中篇小说,我欣然接受,那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战争文学作家了,我认为凡是与战争有关的文学活动,我都有责任首先表态。但是真正进入构思状态,我才发现这不是我的强项,我对于古代战争的生活体验接近于零,创作激情接近负数。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费了很大力气,几乎把十几卷《中国古代战争史》浏览一遍,终于找到了感觉,写了一个“上战不战,上谋不谋”的中篇小说《决战》,王瑛看后拍案叫绝,说这个作品可以获大奖。作品付印之后,王瑛率领我和汪守德、张为、庞天舒一干人等,到东北搞了个采风。路上王瑛津津乐道《决战》,讲到了我的战争谋略,广州军区作家张为表示怀疑,我们在火车上表演心理战,猜“有”和“无”,他出我猜,猜对十之七八,我出他猜,多数南辕北辙,张为于是得出结论,徐贵祥“善诈”。后来果然被王瑛言中,《决战》获得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从此拉开了我不断获奖的序幕。当然,这同王瑛和《解放军文艺》的大力宣传、鼎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八竿子也够不着那个奖。再往后,我同《解放军文艺》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我记得上个世纪末,王瑛约我写一个创作谈,并配发了一张我第一次授衔时的照片,摄于山东长岛,一个上尉坐在山顶一块石头上,头上是蓝天白云,背后是宁静的海面,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我与大海,一起宽阔起来。
2005年,我出版第一个小说集《弹道无痕》,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弹道无痕》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在军内外获得不少奖项,在当时,很多部队老兵复员、新兵入伍都要把这个片子拿出来放一放。我写了一篇创作谈《地铺上的梦想》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不知道是表扬还是批评,王瑛说,这是一篇很像小说的散文,也是一篇很像散文的小说。
岁月荏苒,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解放军文艺》发展军事文学、扶持军队作家的宗旨没变。编辑人员也一茬一茬地更换,我最初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离开了,只有王瑛像种子一样牢牢地扎根在这块园地上,从编辑到副主编,再到主编,而我,也从解放军出版社调到空政文艺创作室,再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主任。
我调回军艺工作之后,很快发现一个现象,文学创作教学,理论家讲课往往隔靴搔痒,作家往往会写不会讲,那么,恰好是文学编辑,阅稿无数,既有鉴赏水准,也有表达能力。在计划聘请校外指导老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王瑛。当然,聘请王瑛,还有另一个意图,那时候我有个想法,要把学生的作业打造成作品,要在军内外刊物上陆续发表。这个意图被王瑛一眼看穿,起初犹犹豫豫,怕我给她上套,但禁不住我软硬兼施,最后只好参与进来。
2013级招生结束之后,为了强化学生的创作意识,我决定从他们穿上军装开始,即布置创作作业,直至达到发表水平。要知道,我的学生都是刚刚毕业的前高中生,部队生活不熟,艺术风格尚未成形,连基本的写作训练都没有经历过,要其作品达到发表水平,确实有些揠苗助长之嫌。我明明知道这一点,仍然一意孤行,确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希望在“揠苗”的过程中把我聘请的校外指导老师和我的学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长治久安。
王瑛看了稿子之后对我说,差距太大。我说,没有差距,要你我干什么?
王瑛说,你这个人真不讲理。我说,当年你约我写《决战》的时候,我的基础还不如这些学生。你这样的编辑,我这样的老师,强强联合,哪怕是个猴子,我们都能教会他写小说。王瑛笑笑,带着她的助手吴述波和唐莹,一遍一遍地看稿子,一遍一遍地跟学生谈,一遍一遍地改稿。文学系的会议室成了他们的第二办公室。经过反复打磨,那些稚嫩的稿件终于像模像样了,确定在《解放军文艺》2013年12期刊发文学系新生专辑,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有益的锻炼。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王瑛如释重负地把手中的稿子往面前的桌子上一放,似笑非笑地说,我这一辈子,算是和军艺文学系绑在一起了,我的前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后半生用来培养徐贵祥的学生!
我喜出望外,连忙接上去说,好,一言为定!